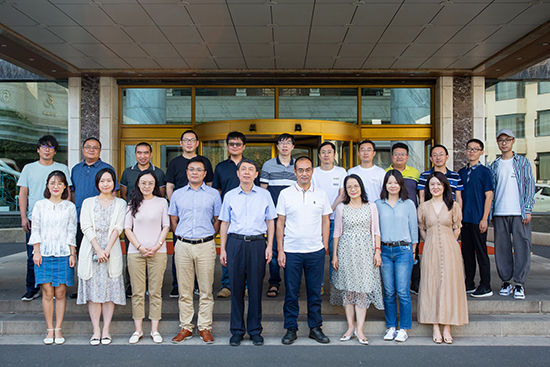江苏作家网讯 2020年9月12日,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在南京召开。本次活动由《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钟山》编辑部联合主办。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钟山》主编、《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及省内外近20位青年批评家等参加了会议。

汪兴国在讲话中回顾了论坛举办的历程,肯定了前三届探讨的议题“长篇小说的现状与问题”“当代文学的共识与分歧”“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当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类型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等在文学界产生的积极影响。今年是《扬子江文学评论》正式更名创刊后举办的首次论坛,作为我省扬子江文学系列品牌活动之一,论坛旨在进一步发掘青年批评家的话语力量,通过青年批评家的新锐视野,聚焦新鲜文学现场的前沿热点话题,引领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新方向。汪兴国在讲话中对当下文学批评提出期许,希望新时代的江苏文学批评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充分发挥激浊扬清的重要作用,及时关注、主动走入活跃火热的文学现场。
本届论坛讨论了“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当下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三个议题,三场讨论分别由《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王晴飞、《钟山》副主编何同彬和省作协创研室干部韩松刚主持。
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
王晴飞提出,文学秩序与现实是有机互动的关系,新的生活秩序和思想感觉会伴随新的表述形式,新的表述方式也会带来新的感觉和观念。由此会看到先锋文学带有明显的过渡性,先锋浪潮之后,文学对现实的表现必然发生明显变化。






而正是关于先锋写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及其之于后来写作的影响,引起了批评家的不同意见。《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认为,先锋文学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和影响主要在于审美体系和知识体系层面。学院派批评体制及各种新理论、新概念的涌现,肢解了先锋浑然一体的美学理念和探索精神,遮蔽和窄化了同时期更宽阔、复杂的写作谱系,导致对先锋的理解越来越狭隘。在方岩看来,如果写作本身产生的未完成事件跟未完成的历史与现实之间能够不断形成对话,就是一种先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路内的《雾行者》、李宏伟的《灰衣简史》、张忌的《南货店》等都是近年来有益的写作尝试。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不完全同意方岩对1985年前后这批先锋派作家的评价,但他也认为有必要重新厘清关于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的模糊认识。他对先锋派的背景和特点作了梳理,指出先锋派本身是一个不确定概念,它是一种姿态,永远像急行军一样走在前面。同时,他认为文学无法超越现实,只能不停地追赶现实,正因为现实在不断变化,文学才需要不断更新,才会出现先锋文学。先锋和现实的理想关系应该“外在是现实的,内在是先锋的。”
尽管对先锋文学的界定和评价不完全相同,但青年批评家们都认同先锋不能局限于文本实验。南京大学教授李章斌从诗歌角度阐释了这一问题。他结合张枣的《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展开分析,认为“元诗”概念本就有自我指涉的倾向,很多当代诗人迷恋语言神话,强调语言的自足性,这在提升语言探索自觉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切断了语言之外的世界。他对这一诗歌观念进行了拨正,提出真正的创造性语言,需要在历史、现实、社会的持续交流中,相互激发。
今天回望先锋文学走过的道路,还是希望为现实书写提供新的路径和启发。暨南大学教授申霞艳认为,对于经历过先锋洗礼的作家来说,寻找某个句式和概念也许并不难,但真正写出具有探索难度和丰富意蕴的作品却不容易。信息富集的时代一方面使得故事频频涌现,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方面也对作家呈现现实的能力提出挑战。石一枫的《世间再无陈金芳》和薛忆沩的《空巢》都写诈骗,但故事放置的语境不同,所铺展开的现实层次也就不同。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颜炼军从杭州杀妻案谈起,就如何将现实经验转化成文学作品作了深入阐释。他认为,现实是一个诡异的变量,不同的语言、形式、风格的作品呈现出来的现实都是不同的。作家需要研究生活,但作家说到底是要通过语言来映射世界,研究生活还是为了通过改变语言来改变世界。
青年写作中的乡村与都市
关于乡村与城市的写作划分,何同彬认为,在城乡转型的大背景下,城市和乡村似乎都难以成为一个自足的叙事空间。不过从经验层面上谈论城乡书写仍有意义,文学如何真实反映城乡经验也确为今天的一个突出问题。




何为真实的城乡经验?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刘大先对曾在走访过程中见到的内蒙古、广西、湖南等地的乡村面貌作了生动的描述,认为这些看似粗粝的、急功近利的、被认为破坏了原生态的景观恰恰也是乡村面貌的一部分。当下的城市和乡村正经历巨大变化,有些城市是类似城乡接合部式的存在,它不能被理解为乡村的升级版,也不能看作是城市的未成熟状态,它是一个独立的然而在不断变化的状态,写作者无法以乡愁式感悟来认识当下乡村问题,也无法以典型想象容纳所有城市经验。这种粗糙的、不符合符号化想象的未完成状态、半成品美学恰恰是写作者要去接受和认识的。
乡村和城市并非某种景观和符号的堆砌,这一点在现场批评家之间形成了共识。那么,文学作品如何呈现城乡经验?《文艺报》编辑行超最近阅读了萨莉·鲁尼的《聊天记录》和《普通人》,这些作品“没有咖啡馆、霓红灯”,看起来是非典型性的城市书写,但这种充满个体化经验的作品反而传达出了真正的城市精神和城市气息。从这个意义来说,行超认为,青年作家王占黑、班宇的作品虽未被归入都市文学,但其中涉及的经验和精神与城市息息相关,这些作品也许更能代表今天所谓都市文学的样子。
远离符号化景观,传递真正的气息和精神,意味着要摒弃同质化的不假思索的写作。在苏州大学博士生牛煜看来,这却构成了当下城乡书写的一层困境。他勾勒了现代文学史以来关于城乡的二元书写经验,并由这条脉络过渡到今天的文学书写。他发现,由于新媒体信息的影响,大家表达的欲望形态和现实经验,以及表达经验和欲望所用的语言、方式都日趋同质化。他认为,写作者要从这种同质化表达中突围,必须在表面的生活秩序之下看到细节,看到深层次东西。
对此,何同彬也结合“梁生宝的账单”和《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新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无论书写什么,作家首先要深入了解书写对象的经验、处境和生活。缺乏坚实的现实经验,再精心构筑的文本也是脆弱的。
当下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讨论看似松散,批评家分别从各自的关注领域触及该议题,实则丰富了这一问题的讨论维度。苏州大学教授房伟不仅从事文学批评,近年也涉足历史小说创作。他在发言中细致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日本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发展线索,提出创作历史小说必须要让历史与现实进行不间断的对话,好的历史文学应该既具有民族特点和民族精神,也能传达某种普世性的东西。






《大家》杂志主编周明全对“为文学而文学”的说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作家的首要责任是要对历史和现实负责。他以莫言的《檀香刑》和《生死疲劳》为例,提出只有把历史、现实、文学三者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出真正的好作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杏培则另辟蹊径,从分析文学作品中好人和坏人的命运入手,透视文学对现实的回应与关照。沈杏培注意到,当代小说里有两种鲜明的人物形象,一种是无用的好人,一种是盈余的恶棍,这些作品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叙事,对新的现实困境和道德困境作出了思考。他深入分析了这种善恶叙事的现实起源,肯定了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回应现实的努力,并希望作家可以从中建立抗恶伦理,体现文学的思辨、关怀和价值。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由周恺长篇小说《苔》的文本价值谈到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她认为,周恺通过这部小说展现了四川乐山一带在外部世界涌入前后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一过程中当地人与外界的种种互动。看似是遥远的革命历史叙事,写作者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是自我身份和自我确认问题。岳雯提出,“不论是写历史还是现实,根本的是要解决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切中我们所处时代的核心问题——这样的小说,是今天真正需要的小说。”韩松刚对此进行了补充,他注意到当前青年写作多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作家局限于个人生活和个体情绪中,缺乏岳雯所说的“照亮现实”的东西,但写作者对自我的呈现、对现实的追问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张博实则回忆了自己和历史系同学的交流,他发现,某段历史或某个历史人物可能是无限复杂的,所呈现的面貌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文学在书写历史和现实的时候,必须对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有清晰的体认,不能用刻板印象来看待和处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贾梦玮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今天的三个论题有两个关键词:"现实"和"现实主义"。他感慨,中国的“现实”确实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现实”。我们的社会和人生是“深刻”和“幽邃”的,这确实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富矿”。但优秀的文学从来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反映,即使是像镜子那样精确,也不可避免地流于表面。他表示,现实有时是作家的“伴侣”和“参照”,更多时候还可能是作家的“对手”,因为作家对现实人生采取的是一种审视、反思的态度。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总是试图创造另一个世界,使之成为现实的参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现实最好的参照,读者得以透过作品反观现实和自身。现实主义与现实之间是一种隐秘、曲折的关系。作家和现实题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自然”的——自然“恋爱”、“结婚”、“孕育”,一朝“分娩”。它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外部力量的刻意“扶持”,走马观花式的体验生活,以及种种“命题作文”,把文学创作弄成了“代孕”。好多作家“代孕”多了,反而不会生自己的孩子了。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文学的现实主义一直面临诸多挑战。(文/俞丽云;图/丁鹏)